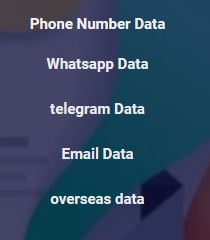欧洲法院或人权委员会已经受理过许多具有这种域外因素的案件,其中每个人,包括被告国,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该条约适用。例如,没有人怀疑《欧洲人权公约》第 6 条的公平审判权适用于缺席审判但潜逃到另一国领土的人(例如,参见Markovic v. Italy)。事实上,不适用公约似乎明显是武断的。如果是这样,那么隐私权又有什么不同呢——问题是哪种理论涵盖了这类情况。
第一种选择是用空间模型来处理这种情况,这是有问题的。第二种 在澳大利亚的海外华人数据 选择是用个人模型来研究它们。但是,如果我们接受 这样的事实,例如,当英国特工搜查我在诺丁汉的公寓时,即使我在英国境外,我也是在英国“权力和控制”之下的个人,那么我看不出我们怎么能否认,如果英国特工搜查我在密歇根州安娜堡的公寓,我也将处于英国的权力和控制之下。同样,如果《欧洲人权公约》适用于即使我在美国也对我的电脑进行搜查,因为在进行这种搜查时,英国对我行使了权力和控制,那么我看不出为什么《欧洲人权公约》不适用于英国特工在美国对我的笔记本电脑进行的类似搜查。换句话说,在个人模型的逻辑下,个人和干扰的位置似乎都无关紧要。
第三种选择是说,我们这里所说的是产生域外影响的领土行为,这种思路可以追溯到斯特拉斯堡的Drozd 和 Janousek案。但在我看来,这并不是概念化人权条约应用的合理方式,因为在每种情况下,人们都可以在领土行为(例如 1999 年北约政府在其领土上决定轰炸塞尔维亚)和域外后果(例如轰炸本身)之间建立某种因果关系。
- Board index
- All times are UTC
- Delete cookies
- Contact 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