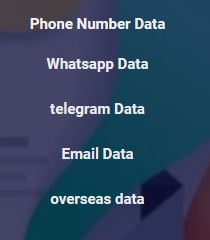其次,同样地,法院认为,事先的司法授权对于大规模拦截的合法性并非必不可少,这也与隐私权活动家所主张的相反,即使事先的司法授权可以被视为最佳做法(请注意,根据新的 2016 年《调查权力法》,,其中既包括部长,也包括独立的准司法专员)。
以下是关键段落(警告——判决书的摘录会使本文很长):
法院明确承认,国家当局在选择如何最好地实现保护国家安全的 Instagram 数据库 法目标方面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见上文引述的韦伯和萨拉维亚案,第 106 段)。此外,在韦伯和萨拉维亚案以及Liberty 和其他案中,法院承认批量拦截制度本身并不超出这一范围。尽管这两个案件都已过去了十多年,但考虑到法院在判决中的推理,以及考虑到许多缔约国目前面临的威胁(包括全球恐怖主义和其他严重犯罪的祸害,如贩毒、人口贩运、儿童性剥削和网络犯罪)、技术进步使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更容易在互联网上逃避侦查,以及电子通信传输路径的不可预测性,法院认为,决定实施批量拦截制度以识别迄今未知的国家安全威胁,仍然属于各国的自由裁量权范围。
然而,如前所述,从法院数十年来的判例中可以看出,所有拦截制度(包括批量拦截和定向拦截)都有可能被滥用,尤其是在当局的拦截自由裁量权的真正范围无法从相关立法中辨别的情况下(例如,见上文引用的Roman Zakharov案和Szabó and Vissy v. Hungary案,第 37138/14 号,2016 年 1 月 12 日)。因此,虽然各国在决定何种拦截制度对保护国家安全是必要的方面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但在实施拦截制度时赋予它们的自由裁量权必然会更窄。在这方面,法院确定了批量拦截和其他拦截制度都必须满足的六项最低要求,以便具有足够的可预见性,从而将滥用权力的风险降至最低(见上文第 307 段)。
- Board index
- All times are UTC
- Delete cookies
- Contact 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