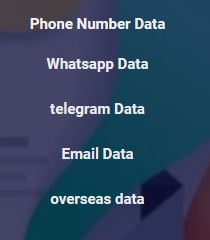Marko Milanovic 博士在劍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撰寫了《人權條約的域外適用》(牛津大學出版社,2011 年)一書,對國際和國家法院及委員會關於人權領域國家義務域外效力的判例進行了出色的分析。這是迄今為止就這一主題所寫的最全面的書,而且我毫不懷疑,它將很快成為有關人權和域外管轄權的標準參考文本(如果它還沒有成為這樣的話)。可以預料的是,特別是對於那些關注米拉諾維奇早期該領域著作的人來說,他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關於人權義務域外效力的判例法是無可救藥的詭辯和無原則的,因此是前後矛盾和令人困惑的。此外,他認為,歐洲人權法院關於域外管轄權的主要裁決——Bankovic訴比利時案(2001)——建立在錯誤的法律基礎之上,與先前的 資料庫資料庫 案件以及核心人權價值觀相悖。
米拉諾維奇對造成這種不幸狀況的大部分原因的診斷是正確的:有關人權域外適用的爭論陷入了理想(人權的普遍性)與政治現實(有效性原則,反對規範的過度延伸)之間的科斯肯涅米式的緊張關係。事實上,儘管邊界和人類福祉之間的聯繫很脆弱,但人們仍然能夠發現,在確保有效保護人權的需要(例如透過消除法律「黑洞」)與繼續致力於將領土作為國際法律秩序的組織原則之間存在著平行的緊張關係。第三個矛盾涉及法院與政府或法律與政治的製度關係,米拉諾維奇曾多次談到這一矛盾,這進一步複雜化了有關人權義務域外效力的辯論。雖然國家權力在域外投射本身並不是一個新現象,但透過法律規範,尤其是透過法院適用國際法律規範來規範國家權力的投射,卻是一個相對較新的發展。因此,法院經常將域外管轄權視為初步管轄權問題(米拉諾維奇正確地批評其為分類錯誤)也就不足為奇了——裁決權是法院為避免政治上不利的決定而採用的主要工具。
無論如何,我同意米拉諾維奇的觀點,即法官們對國家可以自由地在境外對外國國民(更不用說對自己國民)實施暴行的想法感到不滿。同時,這些法官又不願意向政府(尤其是本國政府,就國家法官而言,是本國政府;就國際法官而言,是多國環境下的政府)施加繁重的人權義務,因為這可能會使本已困難的國際幹預變得更加複雜(例如英國對伊拉克南部的佔領,以及北約在科索沃危機期間對塞爾維亞的干預)。
糟糕的案例會造就糟糕的法律,但糟糕的法律書籍卻能造就優秀的法律書籍!
-
chandonar0
- Posts: 595
- Joined: Thu Dec 26, 2024 4:25 am